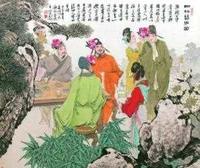在新版《水浒传》里,有许多梁山好汉聚会的镜头,稍微细心的朋友也许会发现,这些英雄们经常在鬓边戴了一枝花,有菊花、芍药、芙蓉,也有各色不有名野花,一帮糙汉子却在头上费心费力地打扮,着实逗人发笑。
甚至还有一特别爱戴花的哥们儿蔡庆,职业是刽子手,绰号却叫“一枝花”,也就是明晃晃地戴花招摇过市,将刚中带柔演绎到至臻。
当然,如果了解一点古代习俗,我们便会知道,须眉男子的簪花历史由来已久,并非水浒英雄们横空出世的团体怪癖,而是宋代自上而下、从民间到贵族都十分流行的男性主流审美。
比如,北宋时期的文人领军苏轼,便曾写下一首诗《吉祥寺赏牡丹》,其中诗句很是生动有趣。
“人老簪花不自羞,花应羞上老人头。醉扶归路人应笑,十里珠帘半上钩。”
此年他37岁,恰值“老夫聊发”的年龄阶段,即使搁在今天来看,年近四十的男人似乎也该成熟稳重、打扮得西装革履,头发即使没有梳得一丝不苟、抹上发蜡,却也不应该插朵大红花?
但苏轼偏偏这样做了,还不以为羞,对自己簪花的举动得意得紧。
引领着两宋时尚的苏轼,发明了东坡巾、东坡帽等物,他推崇簪花自然不是无的放矢,而是紧跟时代步伐,赏完牡丹后,随手便将一朵大红牡丹花插在头上,虽是行得踉跄,却惹来路人和轿中佳人频频回顾,浅笑倩兮。
从文士高官到市井莽夫,爱戴花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习惯,事实上,这一习惯的养成,更与宋王朝最位高权重的一批人——皇室息息相关。
在《宋史》当中,有多处记载皇帝赏赐群臣百官戴花的场景,尤其是在各种盛大宴会上,戴花已经成为一种皇帝赏赐的恩典。
比如大观三年,议礼局安排的集英殿春秋大宴礼仪流程中,就有赐花、戴花的仪式。
“……内侍举御茶床,皇帝降坐,鸣鞭,群臣退。赐花,再坐。前二刻,御史台、东上阁门催班,群官戴花北向立,内侍进班齐牌,皇帝诣集英殿,百官谢花再拜,又再拜就坐……”
止巳、重阳赐宴仪:
“……酒五行,预宴官并兴就次,赐花有差。少顷,戴花毕,与宴官诣望阙位立,谢花,再拜讫,复升就坐。”
“大罗花以红、黄、银红三色,栾枝花以杂色罗,大绢花以红、银红二色。罗花以赐百官,栾枝,卿监以上有之;绢花以赐将校以下。”
从这些记载来看,群臣百官不仅在宴会上接受皇帝赏赐戴花,而且这种赏赐还有等级,不同品级的官员,得到的簪花种类、颜色也有所不同,但都以之为荣,须答谢皇恩。
当然,一众爱花少年、中年、老年中,也有特殊例外,比如《宋史》中就记载了司马光拒绝戴花的一段故事。
“仁宗宝元初,(司马光)中进士甲科。年甫冠,性不喜华靡,闻喜宴独不戴花,同列语之曰:‘君赐不可违。’乃簪一枝。”
司马光少年老成,在一众花里胡哨的男性当中保持朴素作派,也是意料当中事,不过,他的个人喜好,并不妨碍整体风尚,在两宋时代,男性簪花已成共识。
南宋时,宋王朝虽是偏安一隅,男性簪花的爱好依然未变,宋高宗八十寿诞时,百官簪花庆贺皇帝千秋,场景之隆盛,全都被诗人杨万里用墨笔记录下来。
“春色何须美鼓催,君主元日领春回。牡丹芍药蔷薇朵,都向千官帽上开。”
如果说,《宋史》的记载只让我们确定,两宋时期,从宫廷到民间,男性们都流行簪花习俗,而杨万里这首诗,则更加明确地展示了男性所簪鲜花的品种,牡丹、芍药、蔷薇,这些都是艳丽繁盛的大型花朵,可见这些须眉男儿,展示美丽的时候可是毫不吝啬,越是鲜艳娇媚,与男儿阳刚越形成强烈反差,从而形成奇异的视觉冲击。
也正因如此,在《水浒传》里才会出现许多爱戴花的英雄,即使是上战场与敌交锋,那也是“头巾畔花枝掩映、金翠花枝压鬓旁”,不仅自己得意非凡,敌军也见怪不怪,将此视为男性再寻常不过的打扮。
那么,为何在男权社会却会出现这种“伪娘”的男性审美?这与今天对“娘炮”男明星涂脂抹粉的抨击几乎是天壤之别。是两宋男儿不够孔武阳刚?还是历史传承如此,两宋时期经济发达,因而更注重个人装扮?
屈原在《离骚》中便写道:“扈江离与辟芷兮,纫秋兰以为佩。”《九歌·山鬼》中也写道:“被石兰兮带杜蘅。”
可见,在屈原的时代,就已经流行佩戴秋兰、杜蘅等植物,不过这时还没有将花草戴到头上的习惯,而大多是随身佩带,浸染植株清新香气。
两晋时期,人们逐渐流行茱萸插头的习俗。
西晋周处所著《风土记》中便记载道:“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,俗尚此月折茱萸以插头,言辟除恶气而御初寒。”
茱萸是什么?那是一种可入药、也可入味的植物,果实为红色小珠,一枝上常结为数十粒茱萸果,插在头上,便如女子珠宝饰物。
至此,魏晋名士们开始流行起往头上插花装饰。
南朝梁简文帝《答渝侯和诗书》中就写到:“九梁插花,步摇为古。”
步摇是古代女性头饰的一种,但这里的步摇却非头钗,而是一种步摇冠,为男子所戴。
相传,鲜卑族中的慕容姓氏,便是因为他们喜欢戴这种步摇冠,便被人称为“步摇”,后来言语传播有误,便演变为谐音“慕容”。
而与之相应的,九梁插花,也明确是指的男性。
九梁,是指朝冠上装饰的九条横脊,当然,并非所有的官员朝冠上都有九梁,梁数多少,是视官位高低而写。不过,无论梁数多少,九梁插花,也都是指代在朝冠上插花,这与两宋时大为盛行的男性簪花风尚就极为相似了。
因此,在翻看这些古代典籍时,一定注意甄别,千万别误会插花、步摇就是女性头上的装饰,事实上,须眉男儿爱美之心,也不遑多让。
古代科举考试中,殿试第三名叫作“探花”,而这个名头的由来,便与男性簪花有关。
唐代新科进士放榜时间恰逢春季杏花盛开时节,皇帝会在曲江赐宴游园,名为“杏园宴”。宴会当中,将挑选两名年少英俊的进士为“探花使”,负责采摘鲜花,迎接状元。
想那进士饮宴,一群朝廷准官员与鲜花为伴,各自在头上插满红白花朵,醉意微薰,不时有名句吟唱,诗意、酒意、春意俱混为一体。
因为有了探花之雅,达官贵人们热衷于赏花、戴花,唐代花市也因此繁荣,这才有了刘禹锡的名句:“有牡丹真国色,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
洛阳牡丹一直引以为傲,头戴牡丹花,也成为洛阳人的习俗。
宋代欧阳修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便记载:“洛阳之俗,大抵好花。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,虽负担者亦然。”
如此看来,洛阳的牡丹有贵有贱,却是人人都爱的花儿,连挑担子的苦力都会戴花。
经历两宋全民戴花的洗礼后,时光之舟逐渐推向明清时期。
在新的时代,男性有了新的审美,但依然有着令现代人吃惊的表现,比如传自朝鲜的马尾裙,下摆蓬松张起,宛如一把伞。
不过,尽管明清男性衣着上仍有许多讲究,两宋时男性往头上戴红白大花的习俗,却逐渐淡去。
明清时的男性,并非不戴花,只是戴得比较含蓄、内敛。
比如每年三月三日,杭州城内便有大批男性聚集,共戴荠菜花游春,甚至还流传下“三春戴荠花,桃李羞繁华”的名谚。
三春,也就是农历三月,因为这是春季的第三个月,故而称为季春,也称三春。
何为荠菜花?这是一种在南方漫山遍野生长的野菜,俗称“铃铃草”,可入药、入菜,花呈白色,细米粒状,可说十分不起眼,与牡丹之流完全不能比拟,却也另有一番质朴风味。
此等盛景,在明代田汝成所著《熙朝乐事》中也有记载:“三月三日,男女皆戴荠花。”
清代顾禄在《清嘉录》中也有引用,足以证明,戴荠菜花游春的民间习俗流传甚广,被普通老百姓广泛接受。
想象一下,满城男男女女,不分老幼,都顶着一头的细碎小白花,一起踏青游玩,虽然没有大红艳丽的色彩冲击,也不失青葱绿色中的一抹小清新。
端午节,人们常在鬓边插茉莉花。而立秋时,男女则皆戴秋叶,又或以石楠叶剪刻花瓣,扑插鬓边。
如此看来,在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,不可轻易毁损”的古代,长发飘逸的男性同胞们,在头上所花的功夫,半点也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女性。
无论是先秦时的“佩秋兰、戴杜蘅”,又或是两晋南北朝时“九梁插花”,盛唐时的“探花游街饮宴”、两宋时全民簪花狂欢,明清时淡雅朴素的节日应景,男性簪花习俗从历史长河中悄然探入、兴盛,又逐渐销声匿迹,甚至到如今成为一件令人惊讶的怪癖,这都是文化和审美的不断变迁。
时尚是个循环的怪圈,如今在对着众多化妆打扮的“娘炮”炮轰时,不妨反思一下,这是否也是历史的自然选择?亦或是对往昔的复古回溯?
毕竟,审美这东西,有太多主观因素,当绝大多数人都引以为美时,那便是美了吧。即使男性簪花,也不过司空见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