柯云路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,当我高中读到他的《新星》时,我被彻底震憾了,觉得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较好的作品。
主人公李向南是一颗在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,他在古陵县城进行一系列大胆的改革,触动了古老土地上的沉重枷锁,也触碰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“奶酪”,因此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抵抗和斗争。而李向南,具有足够的智慧和政治手腕,每次都能举重若轻地击败对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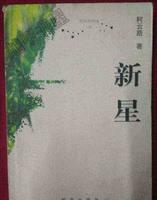
正值崇尚英雄主义的年纪,我轻易就被李向南的个人魅力虏获,成了他的忠实崇拜者。以后很多年,我心中有一个愿望,就是成为李向南式的人物。他的那句座右铭“百折不挠,愈挫愈奋”,也一度成为我遭遇人生挫折时较好的疗伤良药。
读了《新星》,崇拜李向南,十八九岁的我身上有了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。我觉得我洞察世事和人性,把周围的一切人和事物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——小说赋予了我李向南那样的像X光能透视的目光。
一次,我在家里向对面看去。对面的大楼突然出现一个老者,他定定地站在窗口,以居高临下的目光审视着我——我家住三楼,他家大楼是五六楼,刚好给了他一种这样看我的目光。我不甘示弱,也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他,大家就这样对峙了十多秒。十多秒很短,但在人类中间、尤其是陌生人之间,是一种心理较量,互相打量之下,分析着对方的经历、身份、性格等,一较高下,希望在气势上压倒对方。
十八九岁的我能有多少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?只是像有李向南的灵魂附在我身上,才让我有底气与一个长者进行目光对视和较量。
目光对峙中,后来对方先移开了目光。很多年后我才明白,这并不是我的胜利,恰恰是我的不成熟和失败,因为,对方的主动转移目光是一种强者的智慧之举——只有层次高的人才不会无端地陷于和对方无聊的对峙中。
和烂人纠缠,一点意义也没有,反而把自己的层次拉低了。
很多年后我反思,我十八九岁时的那次目光对峙,只不过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伪成熟。那时的我,实际上还幼稚得很。
柯云路的小说《新星》被拍成电视播放后,上演了那个娱乐匮乏年代才有的盛况:一出戏足以引起万人空巷。遗憾的是,我没能追剧,原因很简单,仅仅在于父亲对电视机的“垄断”。电视机在他的房间,我那时住八中这边,回到烟厂的家,惯常便呆在兼作姐姐卧室的客厅。我挺喜欢看电视,在电脑、手机发明之前,能提供丰富多彩、引人入胜精神产品的电视机,曾是多少人的心头之爱。,一般,我只趁父亲不在的时候,偷偷溜进他那间由老家具包围、透着陈腐气息的卧室,坐在那张老掉牙的沙发上看电视。看着看着,他从烟厂下班回来,尽管我对电视有着千般不舍,但还是会乖乖起身离开。
从小不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我,对他一直有着隔着一层似的疏远。两个人坐在一起,我会觉得不自在。
演李向南的是周里京,演女主人公林虹的是演员刘冬。那个年代,正是电影杂志《大众电影》如日中天的时期,被全国人民所追捧。每期杂志一出,我就会到紫林庵街边铁皮小屋做的报刊亭,从有限的生活费里挤出一点钱买一本。刘冬有一张照片让我十分景仰和喜欢,她穿着一件用醉人的面料做成的裙子,光彩照人,有一种独特的美。她的脸型不是女性较好看的瓜子脸或鹅蛋脸,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美丽。
《大众电影》封面用的是繁体字,学识不够的人经常会把“大众电影”念成“大家电影”,我初次看到这几个字,也误以为是“大家电影”。这样的笑话经常会在身边发生,引起一阵欢快的笑声。每期《大众电影》我都不会落下,除了刘冬的那张照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外,还有李玲参加某个会、在台上讲话的照片也让我牢记一生,照片上,她粉装玉琢一般,玲珑剔透中顾盼生辉。
那时我选照片只有一个原则,专找漂亮女演员挑。
外国人的名字是我这生最怕记、最难记的,但有一个当时出名的外国女演员让我记住了,叫菲比凯茨。照片上她穿着一件当时国内还不大敢穿的超短裙,两条健康修长的大腿亭亭玉立,摇曳生姿。我经常盯着她的照片看,甚至脑中想入非非——要是她把身上的超短裙掀开,那将是一种怎样诱人的春色。
我猥琐地给她起了一个名字,“菲比凯茨•一掀”。
柯云路在写出震世的代表作《新星》之前,已有不错的作品问世。我看过他刚步入文坛时写的《孤岛》,这同样是一部个人英雄主义的作品,主人公也是一个像李向南一样能面对一切困难、处理一切问题的英雄式人物。在火车驶入一个小岛,被暴风雨淹没成为孤岛后,发生了一系列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冲突和悲欢离合。
柯云路擅写各类超越平常生活的英雄人物,他写的这些人物,很早就成了我的偶象。
那时我自以为的初恋对象,鄙夷不屑地对我弃之不顾,这令我十分痛苦,心中苦水泛滥之时,年轻富于想像的大脑便时时构思这样的情节:哪一天贵阳也发大水了,我们也被困在“孤岛”上,我泅水游过去救她。在烟厂宿舍和银行宿舍之间,积日的暴雨已然形成一片,暴雨仍然没有止歇的迹象,一切变得越来越不可控,越来越危险,好像世界的末日就要来临。我从淹没三楼窗口的水里跳出去,张开双臂,奋力向她游去,将陷入惊恐中的她救了出来。望着她美丽眼睛中由惊恐而放松的神情,我默立一旁陷入沉思:我不相信,我救了她的命,她会不感动,此情此景,即便铁石心肠也会软化……
遗憾的是,后面贵阳一直没发大水。我英雄救美人之后抱得美人归的宿愿,也就久久无法实现。
在《新星》之后,柯云路接着写了续集《夜与昼》《衰与荣》,都极为精彩。柯云路是文坛的奇才,对人物的刻画和心理描写,短短几笔,几个极普通的词语,就能描摹得穷形极象,让我不能不感叹他这方面的天赋。如果柯云路继续走这条路,在中国的文学史上,他将占有一席之地。遗憾的是,写着写着,他画风突变,开始写起人体特异功能来了——《黄帝内经》。
这可能是他被时代裏挟之下的糊涂之举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气功、人体特异功能热在神州大地盛行,作为作家的柯云路不能免俗,用他的一支笔参与到这一荒唐的队伍中。气功、特异功能骗子层出不穷,不仅骗遍华夏大地,甚到骗到中央。从今天的角度来看,在科学文明昌盛的二十世纪,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有点让人匪夷所思。
我在贵阳街头,亲眼看到了意念治病的荒唐一幕。在紫林庵那儿,有一个干巴老头在街边摆了一张竹椅子,号称能用意念治病。有相信和盲从者信以为真,安安静静地坐在竹椅子上任由老头摆布。只见老头拿出一面小圆镜,对着镜子,眼神发直地念念有词。我看这面小圆镜,极为普通平常,在当时花一两块钱就能买到,我家里就有一面。发功的过程中,老头会反复追问“患者”所报的症状好点没有,可笑的是,还真有“患者”说感到他的风湿病、腰椎病等好多了。
一番装神弄鬼后,“患者”乖乖掏出5元钱双手奉上。
其实人体的精神虽然无形,但它确实是存在的。这一点随着年岁的增加,我的感受日益明显,生气时,我的腹部会明显感到一种不适感——这一点在年轻时体会并不明显,这说明精神和肉体真的存在某种关联。信则有,不信则无,“患者”一旦相信老头胡谄的意念冶病,心中就会真的产生一种被治好的若有若无的舒适感。
我家中至今仍摆着柯云路的几部小说,《孤岛》《新星》《夜与昼》《衰与荣》,都称得上是我喜爱的文学作品。在阅读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,想到柯云路曲折的人生,不免会发出感叹。
套用一句现在流行的网络语,“人生无常,大肠包小肠”。
